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前线论坛。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中文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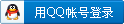
×
石 条
小时候,我家住鸡蛋市,这是本村最宽敞的一条胡同。胡同隔大街对面,稍错开一点,便是大过间。大过间北口靠墙,东西两边,与街道垂直,各放置一块长两米、宽约30多公分的石条。西边的规整,凿工细腻,东边的略显粗糙。
除了冬天,一年春夏秋三季,西边石条上总坐着一位小脚老太太,身下一个蒲团,那是福利的祖母,我叫她二大大。我母亲比二大大岁数小不少,闲暇时,也常坐在石条上,与老太太聊天,家长里短,总有说不完的话。每逢说到紧要处,二大大就会“啧啧,啧啧,你说说,你说说”,不知是赞叹,惋惜,还是遗憾,也许什么都有。夏夜,这石条旁边的大街中央,铺着一领蒲帘子,童年的我,躺在上面,仰望天河数星星,找牛郎织女,指点流星,充满幻想,母亲用蒲扇给我驱赶蚊子。至于她俩说什么,我不感兴趣。
福利的祖父叫刘鸿雁,写一手好毛笔字。家藏的解放后政府发的房地契,就是他填写的。小时候我还见过他,一个高个,身穿便服,说话走路慢条斯理的老头,就住在西边石条紧靠的瓦房里。我跟福利是光腚耍伴,曾在他爷爷奶奶家里,见过二老的写真画像。还有一个日本瓷瓶,非常漂亮,这东西不知现在传承在谁的手里。大约我五岁时,在福利奶奶家院子里,还拍过一张像,母亲居中坐着,我跟姐姐一边一个垂手而立,背景是挂起的一条床单。那时母亲真年轻!
与西边石条隔街相对,鸡蛋市胡同口西边,是刘洪祺家大门。东门垛下,也有两块石头,靠门垛的高,外面的一块低。低的与地面平,上面刻着一幅棋盘。据老人说,想当年,是坐在小凳上,就着棋盘下棋的,意思是说,早先的大街中间是很低的,这棋盘石高出地面一个小凳。现在这块石头已经不见踪影,也许埋在混凝土底下了。高的一块长80公分,宽约35公分,是略呈梯形的随形青石,两头稍高中间略凹,比棋盘石高出40公分。刘洪祺的父亲我叫他大老爹(祖父辈),一个矮个老头,那时还活着,常坐在上面休息。我小时候也常在上面玩耍。我7岁刚上书房的时候,因为没事总咬着铅笔,刺激得两颗门牙中间竟长出一颗小牙。一次,母亲坐在这青石上,往后扳着我的头,给邻居看我畸形的牙齿,印象很深。
福利的爷爷弟兄二人排行老二,过间西的房子福利爷爷住,过间东的房子他大爷爷住,一个过间把两家从空中连在一起,也把血脉永世连在了一起,过间口两块石条也就分属了东西两家。东边的石条上,坐着利生的奶奶。利生是福利的堂兄弟,他还有个哥哥叫太生。他们的父母在济南工作,兄弟二人打小跟着奶奶生活。太生大几岁,个高威武有力气,生产队时年纪很轻就赶马车,后来落实政策接班去了济南。利生的爷爷我即便见过也是刚记事时,后来吃地瓜噎死了。奶奶也是小脚,年事己高,行动不便,所以,利生很小就挎个瓦盆,到西河洗衣服,五冬六夏,未有停歇,从小感受着人生的不易,街坊邻居都叫他“小姑娘”。我俩也是光腚耍伴,有一次,我俩到东埃一条沟里刨“玉皮压兰”,贪玩,竟忘了时间,中午也不知道回家吃饭,直到晚上被大人找到。我好像是没挨打,只被痛骂了几句,利生是被他奶奶用条帚疙瘩结结实实揍了一顿。后来,利生也落实政策,进县城汽车站工作。常坐在东边石条上的利生奶奶,大约那时已经去世了。
1977年我18岁,高中毕业,在生产队推小车,正是有劲无处使的年龄。有一次,我跟老牛叔(大名刘洪乐)在大过间口比力气。拉钩,推手,掰腕,手劈砖,不分胜负,最后比搬石条,看谁能搬起胡同西边这根长石条。我横跨石条,立个骑马蹲裆式,沉臀弯腰,两手左右由下搬住石条中间,一使劲,就提了起来。这石条究竟有多重,至今也不知道,但确是不轻,二人抬也得费大力气。当然,后来老牛叔也一样成功,仍是未分胜负。应当说,那时我还在发育时期,筋骨未定,力气不全,青年气盛,全凭一猛子冲劲。而老牛叔比我年长十岁,正值盛年,身强力壮,我是比不过他的,只是心里不服而已。
1978年,我接替大哥当了大队会计。这年夏天有一天中午,热浪滚滚,令人欲睡,我坐在大过间西边的石条上,东边石条上坐着一位中年妇女,我们说着闲话。这妇女青年时丈夫就死了,上有公婆,下有孩子,她并未再嫁,生活颇不容易。我偶尔瞟她一眼,突然就愣住了。只见她,上身空心只穿一件的确良小褂,上面三个扣子不系,一只丰满诱人的乳房,颤微微地露着大半。读者知道,那时不比现在这么开放,社会风气保守,也接触不到什么黄色东西。我十九岁了,还是处男,从来没见过女人裸露的胴体。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怎么能不脸红?恐怕喘气都不匀了。我想看,又不敢盯着看,只能偷偷瞄上一眼。而她,像没事儿似的,面朝西侧身坐着,左腿翘踩在石条上,搭着左手,右腿自然下垂,暴露的胸部正好对着我。她眼睛看着脚下,管自说她的话。其实,我想她早就知道我的窘态,是故意不看我,故意解开的扣子,让我看她的前胸,目的或许是为获得一种心理的满足。现在想来,可能她长期寂寞难耐,压抑的性需要以某种方式释放,而当时的社会风气,又使她不敢越雷池偷情,这才出此下策。其实,她为了侍奉公婆,养育子女,正值青春委屈自己不再婚,就说明她是个传统、贤惠的好女人,平凡而伟大,但人的本性有时是难以遏制的。虽然以现在的观点看来,她守寡颇不值得,甚至略显愚昧,但以我这岁数的人看来,还是得给她伸大拇指的。
这石条与大过间一起,经年累月,像处子一样不声不响,静静地立在那里。南来北往的小贩,卖香油的,卖雏鸡的,换豆腐的,推车的,挑担的,累了就在这坐一会儿,歇歇晌,与二大大聊几句,随便与家庭妇女做成几单生意;下雨天下雪天,就在过间下避避风雨,天晴了再上路,为生计继续忙活。它们在人眼里是那么不经意,可又不可或缺。
后来我就参加工作进了城,以后又寓居外地、外省,很少回老家了。直到2005年底,我又定居县城,回朱宋老家才又多起来。来来去去,看到那两块石条仍在原处。大约在2009年,村里搞新农村建设,道路、胡同全部硬化,街上的汽车来来往往,越来越多,或许有人感到石条横放阻碍交通,西边的石条被顺着放在北墙屋檐下,东边的不知去向。今年,开车回家进出鸡蛋市胡同,似乎感觉少了点什么。后来才突然醒悟,是那剩下的石条也不见了踪影。一股惆怅蓦地涌上心头,仿佛儿时、年青时的记忆也随着消失了一样,感觉空落落地。
不才今年腊月已虚度六十,昨晚看周作人的散文,就想起了那石条。因了这石条,又想起母亲、二大大、左邻右舍和光腚耍伴。其实,这石条不过是个由头,牵出的是尘封的岁月,遥远的回忆,童年和青春,与石条有关或无关的几件事。我把它们记下来,也是为了留住记忆。这几年,故乡往事,亲朋故交,总是进入我的梦中,就象发生在昨日一般,历历在目。每当这时,心中充满着欢乐、愉悦和幸福。尔来世界变化,天翻地覆,岁月流淌,往事如烟,像春梦一般了无痕迹。有那石条在,那大过间在,就觉得记忆深处的风土人情,是真的,不是梦。可一旦这些东西都不存在了,那些记忆就没了寄托,仿佛随风飘散的云彩,再也收拢不起来,怎不教人好一个心酸哪。
去年写了一年散文,多是回忆性的。忽然感觉,写这些东西,没有什么意义,既无深刻的思想识见,也无令人感动的故事情节,近乎无聊,所以年底就搁笔了。然而一旦看书,勾起回忆,就又不由自主地摸起键盘,想记下来,给自己一点心理安慰。同龄的人,看了这些零雁断篇,残梦旧事,或会心一笑,或点点头说:“嗯,这就是我们的那个时代。”年轻人看了,会说一句“原来那时是这个样子的啊。”这才知道,原来上辈都是吃玉米饼子长大的;这地方原来还有两根石条,石条上还曾经坐着两个老太太。
二O一八年一月十七日
又记:真没想到,昨天上午回老家,发现那两块石条都好端端地在,只是紧靠墙了。看来是我的眼睛或记忆出了毛病。不过,它在我心底形成的波澜,已经真实地存在了。
二O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
附:《石条(二)》(点击阅读)
|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烟台前线
( 冀ICP备13012704号-1 )业务客服: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烟台前线
( 冀ICP备13012704号-1 )业务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