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前线论坛。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中文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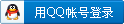
×
本帖最后由 岗山文化 于 2018-4-27 16:03 编辑
常言道“春雨贵如油”。一场不大的春雨给盼雨心切的农民带来了生机,抢墒播种,家家忙得不可开交。 我,如今也成了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这不,乘雨后的良机一大早就上山播种芋头。雨量不大,泥土依然僵硬,抡起镢头,用以往笨拙的方式开沟下种。坚硬的土地,一镢下去仅仅挪动几厘米的泥土。用力用力再努力,双臂累痛了,腰也有点受不住了,可我不能罢休,若不就失去这唯一的时机。此时此刻,往年的情景又出现在眼前。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这是多年来农家的一句格言。如今农民耕种作物及管理果业是以化肥为根基,实行半机械化作业,且收获喜人。然而,就在几十年前世代农民都是每日在用笨拙的工具和泥土打交道,是实实在在的泥腿子庄稼人,统称为不见世面的乡巴佬。 面向黄土背朝天,这是对中国农村历代农民的真实写照。的确如此,昔日的农民,正确的说是近在20世纪70年代前的农民还是靠天靠地吃穿。常言说得好啊,庄稼庄稼,种庄稼全靠“撞”,即靠天,碰运气。土地是命根子,为了生存,整日整日都在泥土中摸爬滚打,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游牧”生活,尤其是男人,山就是家。那时候早饭、午饭都是家里的女人孩子拐着饭篓子,再抵楼(提)着小坎(小罐子装着水或汤米)向山里送,晚上墨黑才回家,鸡叫头便就上山。曾经有个笑话,一家孩子都六岁了不认识爹,一日见了他爹认为是外人竟往外赶。因平日天不亮就上山孩子没有起,夜里回家晚孩子已睡下,一直未见面。 当年的农民过着没白没黑没节假日的单一生活。常言道:刮风拾石头,下雨槎草绳。地处山耩薄地兔子不拉屎的地石头多,刮风天别的不能干就上山从地里向外捡拾石头,下雨天不便上山就在家里槎草绳以备捆绑山草和庄稼,反正闲不着。其它时间大多在捣鼓泥土上做文章。上山铁锨撅着个提篓子,一是检拾道路上的牲口、猪(放牧的叫看猪)鸡狗粪便,二是防备雷雨冰雹,若遇到冰雹就将篓子扣在头上。春季播种前趁天好在场院拖挤(泥培),晒干后就打炕、盘炕。就是将烧了一个冬天的土炕扒拆,用其当肥料再盘新的。接着就是取粪、刷粪、捣粪,备足下种肥料。盘炕需垒炕的小泥土挤培200个,铺炕顶面的需中间夹带棍的(相当于当今的钢筋)有支撑力的大挤泥培12个,待干燥后打(拆)和盘。日常生活习惯是每日早首先喂牲口、猪、鸡鸭。填料喂食后,就是挎栏(向外搬牲口一夜踏踩的粪便和昨日傍晚垫的新泥土,相当于搅合)、垫圈(垫新泥土),即给牲口栏和猪圈内垫土挖除攒粪。那时候无有钟表,晚上就以喂几合(几次)牲口为计算时间。其次是需每一天傍晚用铡刀铡牲口草、把水缸打满水,备足人畜及防火的水。俗语说:南跑北奔不如拾草攒粪。这粪就是牲口粪便、猪圈粪、炕洞挤、锅头草木灰等。到了冬季首先要备足草烧炕取暖和攒粪。都知“老婆孩子热炕头”农村冬天就是这样过。再是封冻前后在自家地里开沟打泥用牲口链(驮)回家,以备一冬天垫圈垫栏用泥。有句顺口溜是“门口没有三大堆(泥、草、粪)长好庄稼正是吹。捣粪刷粪就是将圈粪、炕洞挤等捣碎刷细,以便播种或追肥用。追肥工具样子像条编提篓子底部(无把,编织密集,不漏泥粪),上部两边有一条宽带子,叫粪斗子。斗子带绕肩横跨在脖子上,装上刷细的粪土用两手向地里撒。生产模式是春季捣鼓粪土,冬季拾草垫圈垫栏。这真是韩宝捣粪越倒腾越少,草庄打柴支呼燎刁,好大的疃无人家,空架子。种地的基粪不用捣刷,从圈里穿着绑取出来,两个人用抬筐抬到自家粪场堆放发酵,耕地前直接用牲口驮到地里(叫链粪,往家驮叫链跺子),杨开粪后再耕地或刨地待播种。 在那个年代,农民全靠一双勤劳长满老茧子的双手和那泥里来水里去的两只铁脚板及压扁了的双肩向瘠薄的黄土地来索取生存养家糊口。穿戴的是自种的棉花经放线后自织的粗布衣。吃的是自家的粮食,用的是家中的产品换回来的油盐酱醋和锅碗瓢盆。夜里点灯的是花生油或豆油及后来的洋油,点火用的是火镰到洋火。三伏天熏烤蚊子是从山里拔来的蒿草拧成绳子晒干后关门点燃,满屋子烟熏火燎。就连小小的虱子和虼蚤(跳蚤)也奈何不得,只得晚上在油灯下用手抓,老人看不见就摸索着用牙咬。房子顶盖的是山草,窗棂子糊的是白纸。冬季那热炕头大半被地瓜占有。那年头,好家庭的可以说能自给自足,年吃年用的占多数,一年下来大多所剩无几。遇到盖房娶亲需紧扎腰带省吃俭用多年,才能将就着过去。如今回想起来不可思议,那些前辈一代代是咋熬过来了的啊!六七十年代我母亲还在用她那陪嫁的平木板织布机纺线织布,1971年我在中学任教时还是用的母亲织的花布被和染匠染过多次的衣裤。星期天有时候我还学着坐在织布机上织布。吃的是粗粮地瓜苞米,一年四季只有大年三十才能吃点好的,年中午能吃上大米干饭,晚上吃点地瓜面或粗面馉馇(饺子)就算是能过年了。好年景能吃上白面馉馇,年景差的除了能做几个上供的大枣饽饽外只能在五更发纸祭奠祖宗做点白面的馉馇浇奠。那时候种点麦子无水浇仅靠那点土肥,收获太少了,一般人家招待客人能做点大卤面条就不错了。栖霞官道北部俗称官道西北利亚的安乐庄村一直流传这样的话:安乐庄安乐庄一亩麦子潢口汤,要想吃顿饼还得不留种。对我记忆最深刻的是瞎麦子地里雀窝多,记得生产队里的大片麦子长的大多一拿手高,那包儿兰就喜欢在这瞎麦子根垒窝。掏雀蛋是我最大的兴趣,一块地里往往能找到五六窝。那胡秫(高粱)往往长不好,瞎了。有句“瞎了胡秫悬了绕子”的歇后语。这里方言指“悬了”即多的意思。就是说那种“王八不抬头”,形状像胡秫,因顶部结的穗子沉重,一直低着头,再者秸秆细长软和可用于缠绕捆绑庄稼秸秆和条子草等,俗称绕(第四声调)子。瞎胡秫密集秸秆细长就自然成了捆绑用的绕子。再者还有遇到不平的事或受到别人欺凌的事有“真他妈悬绕了”的口头语,意思说不能这样忍下去。例真他妈悬绕了,欺负家里没人吗!?那时候一个生产队里真正下地干活的男劳动力不多,除了不用上山伸手露胳膊干的大小干部和老婆孩子在家男人在外靠上交口粮款的“五等家属”外,婆娘们成了主力军,即真正的半边天。干活的少,吃饭的倒多。那年月年年夏季灭荒到头来还是地荒粮食减产,我们还常常能在荒地里捡吃熟透了的鲜脆的甜瓜,可带劲了。大集体那阵子,每年每人秋后决分(决算)能分到几十斤麦子、家里分得几十元钱就能过个好年。记得小时候最盼过年,过了冬天天板着指头算计,因过年能有一件新衣服穿,有好吃的,尤其是能吃上点肉还有压腰钱花。年前母亲拿着分配的“驴票”按给的排号到生产队里的饲养栏里牵牲口推磨压碾备过年。 早年的种植老人们也挺讲究,就说秫子和芝麻吧,言语是:鞭杆芝麻,卧牛秫。即芝麻的株距为一个牲口鞭杆长,那两棵秫子之间能躺下一个牛方可成长。那长果(花生)也是如此,刚开始种植是爬蔓的,间距很大,收刨时需围着圈用叉镢刨,再用筛子过,极其费力气。后来品种改良,有了不露礅的,刨省力。往后又有了八拉罐、四粒红、一窝猴等直到今日的花十七等并采用地膜覆盖耕种,产量和收获才有了很大的改善。那地瓜也是有当初的根细长瓜筋骨多收刨费力到今日的“一窝蹲”。栽种时还采用了“窝里放炮”法,就是在地瓜秧苗栽种的窝里再次加点肥料,产量大大增加。在早熟的麦地里栽地瓜芽叫“二瓜”,在麦后的地里插种早地瓜剪下的蔓叫麦茬地瓜,即“蔓瓜”,留着来年做地瓜种。冬季放在山里的地瓜窖里存放。那管理地瓜的歌谣是:头遍浅,二遍深,三遍不能伤了根(指锄松土)。 1958年,在大跃进中,为提高麦子种植面积和产量,提出了“挖地三尺深土地出黄金”的口号。一是深翻地,二是广积肥源。在挖粪圈、臭水沟、拆旧房等同时,在山里刚收获的苞米地里将“布袋”(带泥的苞米根)垒成许多锅灶就地煮地瓜或做苞米饼子,随后就拆除捣碎做肥料。那时候浮夸风盛行,有位包村下乡督导的公社干部曾说过一时可令人置信的话:产量要巨增就要多下种,若一亩地下2000斤种子,一个粒就只长两个吧何况还不止不就是4000斤。其结果来年不仅没有如愿,且几乎赔了种子。其实如今每亩早种麦子只需20斤左右即可,晚茬也不过30斤,关键是合理密植,水肥需跟上。为挖掘肥源,70年代大兴夏季人造绿肥,就是用鲜草加人粪尿用泥腿搅拌封存,这费工费时的泥土捣鼓虽然有一定效益,可害苦了农民啊。 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技术的提高,世代与黄土地打交道的农民才逐步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开始得到了解放。化肥替代农家肥开始都不认识,就说尿素吧,起初动员会让大家使用,有的被劝说实在无法就答应,待半路上将发给试用的扔掉,直到有人试用见效后才被接受。如今街头巷尾的谈论是,地还是那些地,还少了许多,人口还多了,可…… 科学技术的先导,半机械化的生产,这祖辈与泥土打交道的乡村农民正在向城里的人们生活方式转换,那泥土的芳香必将为广阔的乡村带来勃勃生机。乡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昔日的泥腿子和笨拙的劳动工具将成为历史为子孙后代借鉴。

|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烟台前线
( 冀ICP备13012704号-1 )业务客服: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烟台前线
( 冀ICP备13012704号-1 )业务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