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前线论坛。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中文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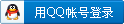
×
豆腐 作者:简
春节前夕,友发了一条朋友圈,记录她学习做豆腐的经过。友文笔细腻,将做豆腐的步骤一一详细描述,隔着屏幕仿佛能闻到豆腐香甜的味道,循着香味我的思绪不由地回到了遥远的童年。
七十年代末的北方农村,秋收之后冬麦播种下去,农活就算忙活完了,勤快的农村人大多闲不住,想方设法找些活计干,给贫困的家庭添点油盐钱。
父亲是个勤快人,手也巧。除了做得一手好木工,还会做一酢(zuo,不知是不是这个字)好豆腐。那时候农村做豆腐的人很多,一大清早,梆子声声,不绝于耳。父亲做的豆腐最受欢迎,别人的豆腐大半个上午过去还剩一半卖不完,天蒙蒙亮的时候父亲才推着一酢豆腐出去,豆腐卖完保准能回来赶上吃早饭。
父亲哼着小调儿推着独轮小车进了院子,把车子停在饭屋(我们那地方在院子里盖的西屋,门口敞开不装门,用于做饭)门口,一边把盛豆腐的从甸子车子上搬下来,一边大声朝北屋(正房,坐北朝南,我们叫作北屋)喊,“饭做好了么?”,“做好了,爹”,大嫂回应道,又回过头来笑着对娘说,“俺爹又赔了一碗豆子。”娘不以为然,揶揄道“要是不赔,就不是他四大爷了!”于是三人哈哈大笑。接下来娘和大嫂张罗饭,爹又去称豆子、泡豆子,准备做下一酢豆腐了。
豆子泡在一个大瓦盆里,中间娘要换好几次水,把豆子淘洗的干干净净。因为但凡有一点点不干净,也是做不成豆腐的。到了半下午大约三四点钟的时候,豆子泡好了,娘把豆子捞出来,把磨洗刷干净,就吩咐我们磨豆腐水了。别小看磨豆腐水,这可是个技术活儿,豆腐水要磨的细,水不能多也不能少,水多了熬豆浆时费柴,水放少了磨推不动豆腐水也磨不细。大哥二哥是整劳力,有其他力气活干或外出打零工去,所以磨豆腐水时往磨眼里添豆子添水这样的技术活儿一般由大姐或大嫂担当,偶而交给放学回家的三哥,我只负责推磨,妹妹是老生子闺女,全家独宠,不舍得让她干活。
磨好的豆腐水一盆一盆地倒进一口八垠(yin)大锅里,天黑下来的时候(大约是五点钟左右吧)豆腐水磨好了,开始烧火熬豆浆。那时没有好柴火,树叶子、干草等就算是好柴了。通常是娘负责烧火,锅底下的火要烧得不大不小不急不慢。娘坐在蒲团上,左手不急不慢地拉着风箱,右手熟练地划拉着一把一把细碎的柴火,像在场院里扬场一样,手一扬一撒,细碎的柴火就均匀地撒在锅底正中央。这边风箱呼哒呼哒有节奏地拉着,锅底下火苗咝咝地舔着锅底。过不一会儿,母亲就用烧火棍挑一挑锅底下已不大旺的火堆,这时火苗呼地一下又窜起来了,随之有许多火星子飞溅起来,像打铁花一样好看。
豆腐水需要熬很长时间才能变成可以喝的豆浆,而要熬成能做成豆腐的豆浆,则需要把豆浆熬得更浓也需要更长时间。熬豆浆的时候,父亲拿着一个长把的大铁勺子,站在锅台旁边不停地搅动,防止糊锅底。如果糊了底,豆腐水就有了糊味,做出来的豆腐口感不好就砸了自家牌子。父亲是顶顶仔细较真的人,对做豆腐也是一样,从选豆子泡豆子,到磨豆腐水熬豆浆,一直到豆腐成品,一丝不拘。这是父亲做的豆腐卖点好的原因之一。
母亲烧火,父亲看锅,我和妹妹则坐在柴火堆里(饭屋里一小半的空间垒起灶台做饭用,一多半的空间用来存放干燥的柴火),一边等着喝豆浆,一边央求父亲或母亲讲故事。母亲讲的时候多,母亲记忆力超级好,一个故事讲来讲去,老是一个样;母亲的语言模仿能力也好,不论是鬼怪故事还是老戏,都模仿的有声有色,惟妙惟肖。以至于妹妹听完故事后不敢一个人进北屋睡觉。
母亲就让我陪她一起去睡,而我还想着喝豆浆呢!于是躺在坑上,我就把从母亲那里听来的鬼故事添油加醋地再讲给妹妹听,吓得妹妹哇哇哭着去跟母亲告状,我则换来一声呵斥,“熊妮子,没个当姐姐的样儿!”于是两人重回饭屋坐到柴火堆里,听父亲讲他当兵时候的趣事,不知是真是假,反正我们听得津津有味(那时候的娱乐活动跟经济一样匮乏,我家连收音机都没有,更别说电视机了。听父母讲故事可能是那时唯一的娱乐了)。
听着听着迷迷糊糊睡着了。突然父亲大声招呼,“孩儿啊孩儿啊(小时候家人对妹妹的昵称,我不配有。)快去关门!快去关门!!”妹妹莽莽撞撞爬起来就往外跑,一会儿跑回来说“爹,门关着呢!”母亲和父亲哈哈大笑,我不明就里瞪眼瞧着。
于是母亲就给我们再讲一个故事,说:一个傻媳妇儿在家熬豆浆呢,开锅了豆腐水直往外沸,傻媳妇儿不知道快点搅和或往锅里添凉水止沸,爬起来就往外跑。婆婆问“你跑啥?”傻媳妇儿说“娘,我去关门儿啊!”哈哈哈哈哈哈,我和父亲听完笑得前仰后合,妹妹又哇哇哭起来。
父亲一边笑着一边不停地用大勺子快速舀起豆腐水,高高扬起再倒下来,不停重复这个动作(很多年以后我恍然大悟,什么是扬汤止沸,这就是了)。等到豆腐水突突突突地光冒泡不再沸出来的时候,豆浆就熬好了。
母亲用一个大瓷盆盛了豆浆,招呼哥哥或姐姐端到北屋里,给家人们喝。父亲则利索地调制卤水蘸(zhan,平声)豆腐脑儿。那时候太小了,记不得具体做法。只知道卤水蘸进去以后豆浆就神奇地变成了白白嫩嫩的好吃的豆腐脑儿。现在想来,那时候我们家虽然很穷,但父母对孩子们真是好的很呢。谁要是想吃豆腐脑儿,父母一点儿也不吝啬,都是满满地盛上一大瓷碗,保准让他(她)吃个够。可是除了我和妹妹,哥哥姐姐们还有嫂子,平常日子里是绝对不吃豆腐脑儿的(那时我以为他们不爱吃)。
父亲拿来专门用来做豆腐的大甸子(好像是用细细的柳条编的,圆形,直径约1米左右,有沿,沿高20公分左右),铺上一个大方纱布(纱布非常大,我觉得至少要大到可以把大甸子包起来),两个大人(一般是大哥二哥)四只手一手拽着一个纱布的角让它形成一个半圆,父亲则用大铁水舀子快速地把滚烫的豆腐脑儿舀起来倒在纱布形成的包里。
再用大纱布紧紧地把豆腐脑儿包起来,一边包一边摇晃(可能是为了加速豆腐脑儿里面的水快速渗出)。包成的形状由大甸的形状决定,包好之后在豆腐上面盖上一个平平的板,再在平板上面压上一个重重的东西(一般是一大铁桶豆腐渣),压重物的目的也是把豆腐脑儿里面多余的水挤压出来,成型后就变成豆腐了。
豆腐的软硬程度取决于压豆腐的重物的重量以及压的时间长短。人家做豆腐一般压个空盆或者重量轻点的东西,做出来的豆腐重量多,豆腐软软的,捧在手里直往外渗水。父亲说,那不行,那样做出来的豆腐一股泔水味儿,筷子也夹不起来啊,吃不到嘴里去。
母亲也不干涉,由着父亲去。结果就是,别人八斤豆子能出三十多斤豆腐,父亲八斤豆子只能出二十五六斤豆腐。那时候家家不富裕,吃个豆腐就算改善生活,买豆腐一定得买做得瓷实的,不像现在的人喜欢吃什么水豆腐日本豆腐什么的。
父亲做的豆腐早晨买回家放到中午,渗出的水也就是盖住碗底,不管你是拿它熬大白菜吃 还是煎着吃,任你怎么拌拉,保准不带碎一锅的,吃头也好。这是父亲的豆腐好卖的原因之二。
早上六点多钟的时候,父亲就起床了。父亲十分爱干净,完全不像那个年代的农村人邋里邋遢不讲卫生。那时候农村人几乎没有人有钱买牙刷(好像也没有卖的),父亲用凉水咕噜咕噜地漱口,在脸上抹上白白的肥皂沫,用手动的刮胡刀把脸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戴的整整齐齐,推着小车又出去卖豆腐了。
父亲不到远处去卖,只在本村和隔着一条小河的叫西李家庄的村子里卖。“梆梆梆,梆梆梆”,街坊邻居们听到熟悉的梆子声,想吃豆腐的人家,或用水瓢或用大碗或用小盆类的容器盛着黄豆出来换豆腐了。父亲拿出秤来(长杆的有秤砣的那种,带一个圆圆的铁盘),换豆腐的人把豆子哗地倒在铁盘里子。
父亲称了豆子,飞快的换算出豆腐的重量(记不得一斤豆子换多少豆腐了),只往多里算不往少里算,熟练地切豆腐称豆腐,称豆腐也往高里称。如果是长辈或者家里很穷的人来换豆腐,豆腐称好之后父亲会再切一小块放进去,说,秤不高,给你加点儿。时间久了,大家伙儿都知道了这里面的门道。于是就有了母亲口头的那句话“换四大爷的豆腐,回家不用称。”(父亲排行四),这是父亲的豆腐好卖的原因之三。
按照行情,如果一酢豆腐该换二十斤豆子(不知道应当换多少),父亲这样里里外外一通操作,最少少换二三斤豆子,这是大嫂所说的“俺爹又赔了一碗豆子。”的由来了。
父亲去世近四十年了,如今忆起儿时父亲做豆腐的情景,幸福的感觉流动在心底,嘴角儿不觉翘起来……
父亲用一碗豆子,一块豆腐丰盛多少家庭的餐桌,温暖了多少个人心,也温暖了我的人生。
(2024年3月4日至3月6日于山东济南法官法院完稿)
|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烟台前线
( 冀ICP备13012704号-1 )业务客服: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烟台前线
( 冀ICP备13012704号-1 )业务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