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上注册,结交更多好友,享用更多功能,让你轻松玩转前线论坛。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中文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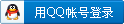
×
想起当年俱乐部 隋建国 过腊八就是年,往日乡村俱乐部那欢快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如今的烟台栖霞人不仅物质生活同全国人们一样大变样了,且文化生活大大高于同等县市区。自娱自乐已是家常便饭,但从家庭来说古人的话“上天堂了。”中老年人跳跳舞围坐炕头看电视欣赏戏曲电影电视剧;青年人在电脑前浏览电视直播和品尝影视点播;手机微信信息交流已是大多人不可缺少的必备工具。这真是应验了“朝廷不出门知道天下事”以往的神话传说。 然而,就在这短短的五十年前,栖霞的人们还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单一的生活方式。业余的生活乐趣就是个把月能看一场县电影队下乡的露天电影。唯一的乐趣,就是乡村俱乐部。每年的大年前后各村俱乐部自编节目出村演出就是那个年代的文化娱乐生活。现回想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六十年代初,当我刚在初中就读时,年假就参加了村里的俱乐部。那时的俱乐部条件很差,只是几个爱好者自发组织的一个群体,还有不少不识字的,其余啥都没有。记得剧本都是手抄的,每个演员只抄写自己的部分,不识字的就靠别人读听记。抄完了剧本大伙就凑在一起按自己的角色对剧词,像课堂学生按角色读课文那样。我家东间那铺冰冷的闲土炕就是我们常聚会的地方。手脚冻麻了,就跺跺脚搓搓手,一点也不觉得冷。剧词熟了就在院之中排练。大家都是导演,你一句,他一言,挺带劲。服装因陋就简或穿自己的或借,道具自做。我和我小哥都是骨干。大过年的家里活忙,可一听到锣鼓响,啥都不顾,撒腿就向俱乐部跑,母亲无奈只好由我们去。 腊月二十三日过小年“徐德堂的老规矩”,俱乐部要在本村进行首场排练演出。台词不熟就安排一人在幕后边一角“提词”。过后继续夜晚排练,直到大年三十晚上。正月初二在本村进行正式演出。从初三起,就出村演出。 在我记忆中,我们村俱乐部演过《李三娘推磨》《龙凤面》《打狗劝夫》《一家人》《井台会》《两块六》《墙头记》《姑嫂擒匪》等剧目,都是吕剧。那些吹啦的都是“半瓶醋”,既不懂韵律也不识乐谱,只是靠听音而已。但他们在台上演奏起来特带劲。个个一边拉,一边眯缝着眼,口中还不停地哼哼,别有一番风味。 那时最感兴趣的是村与村之间的相互演出,直到正月二十前,公社政府怕耽误生产被禁止。有时候还偷着外出回报没有去过的村。不管十里二十里的路程都是步行,服装道具轮换着背扛。道路远的就在傍晚装一点干硬的饽饽边吃边走。每天返回时都是半夜了,还要在一起总结,再就是商定第二天拜访的村庄。每天早饭后那专门负责送幕的就上路了,恐怕被他村占先无村演出。那时的交流也的确是友谊的往来,自己越外出的多,换回来的也多。记得一次已过十五,按规定已经禁止演出活动,但十里外的我们的同族隋家沟还没有回顾。前几年那有名的几位大老板,二老板在我村连续几天的奉送演出,轰动了周边十里八乡的村民前来观看。那《张郎休妻》中的丁香、海棠赢得了掌声四起,至今记忆尤深那能不去回报呢。我们商定避开村和公社的领导,偷偷地将道具送到村后沟内,半下午前头送幕,后边分头出村顺通天河翻上了岗山大北顶直奔东北。那日天未黑就到了,我们就躲在村前高高的龙门口西干渠的渡槽内,唯恐给人家添麻烦。可到底被发现了,村里的人们都出来了往家抢,宾客相待,还直埋怨到了家不进家,很尴尬。那天隋家沟已有十多里外的塔山村俱乐部挂了幕,俩村排演的同一剧目《丰收之后》,目的是相互交流。无奈人家只上演了一场就谢幕,让我们登台演出了现代抗战吕剧《一家人》。
要说出门演剧最热闹的是进村那段时间荣耀,村前都有代表迎接。若本村俱乐部在家就更热闹了。一般当全体人员赶到要去的村时,都在七点多钟,前头提着保险灯(马灯),后边打着两盏汽灯,锣鼓在前,演员在后,待对方迎接。一般等迎接方先敲响锣鼓,再我们接着敲。比较普遍的是打“秧歌皮”,有的是“三翻”。“蹦蹦蹦”三下鼓领头就开锣了。 这一礼节是友谊的象征,双方的锣鼓在比高低。开头是较缓和的曲调,待两队交叉时,各显威风,锣鼓上翻,即“上战场”,以压倒对方的排山倒海之势勇往直前。还有的踏起了高超扭起了秧歌,那领头的吆喝着好不热闹。那时我打大锣,小哥打大镲,一开场我就急敲锣“上战场”。小哥顺手的大镲紧跟,以“紧急风”方式一锤紧跟一锤压倒对方。则对方按常规敲一段时间再翻上“战场”,已经完了三秋,抵不过我们了。呵呵,回想起来多带劲啊!
我们外出像“换亲”一样,一年比一年多。西到招远市的毕郭,南接近莱阳市的谭格庄、西留。东到观里,北到寺口。那时最愿意去的是在官道称为“西北利亚”的几个村庄,尤其是藏在山沟内的仅几十户的迟家沟村。迟家沟离我们接近十里地,从大道转更远。每年我们都是抄近路从岗山上经过。那时岗山上树木比现在茂密得多,再加黑夜,队员们大多比我岁数大,尤其是女的,很害怕。往往把树影子当成怪物向后退,特别是半夜返回时,胆子大的在前,胆小的夹在中间。好几年我们还图方便在岗山水库踏着冰沿河而上。那冰不时的发出一声巨响,“噌”的一下列出一道长长的口子,我们冷不防被吓一跳和沾一身冰凌。
我们之所以都愿到这偏僻的山村,其主要原因是人家“招待的好”。所为招待因有的村看不起这小村,很少光顾。因此有去的他们感到荣幸,再加村里地多,种的花生多,送几盒香烟,几篓子炒好的花生就是上等的优惠。村里人数小围不起场子来,我们就让暂不上台的和其他人到台前充其数量。那次我趁下台的空隙快速数了数台子前共72人,其中还有放在小筐子内的一个小孩。这就是全村的人口了。头几年没有经验,人家给点东西无法拿,后来我们就带上几条麻袋,名义上是用于舞台垫子,其实就是为了往回装东西。有几次在回来的岗山前歇息,每人分几支香烟和几把花生果,我和小哥不会吃烟,就拿回家中等来客用。花生也大部分保留着给母亲。来兴趣了,还在山上敲锣打鼓戏耍上一番。母亲很支持我们,每夜都要为俺兄弟俩等候热饭,那些我爱吃的地瓜、玉米和小量白面带甜头的油炸小鱼都是我的夜宵。
我最初跟大人们演出的是吕剧《李三娘推磨》中的小年“咬脐郎”角色。山东昌邑刘智远赶考途中饥饿交加,偷吃了员外家中的正月十五祭品一只鸡,被发现遭毒打。员外女儿三娘爱其人才与其结亲。后来员外不行跌下马去世,智远进京高中状元,因公务繁忙不能返乡。三娘受其兄长虐待,终日在厢房推磨,不幸在磨道生下一子,用牙咬断脐带,取名“咬脐郎”。好心家人抱着孩子进京。16年后“咬脐郎”奉父命回乡,在井台旁救下投井的母亲。我最开心的是剧的高峰即大结局,我用鞭子抽打这对所谓的坏人“舅父母”,让其二位接替三娘在舞台上转着圈推那用纸糊的石磨,那掌声落幕后还在继续。 反映抗战的剧目《一家人》,我扮演八路军指导员。为拦截营救日军向县城押解的亲人,我们假扮迎亲。我身穿大褂,头戴礼帽,稳坐在轿子内。“趴”的一声枪响,台上烟雾一片。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好几次关键时那在台下用锤砸黄药豆的没有打响,对不上号,全剧的高峰就失去了色彩。又一次我一手向台上摔“摔爆仗”,另一手举抢,挺得心应手,真带劲。若那次舞台地面软,摔不响,那掉落在台下的“摔爆仗”惹来好多孩子哄抢,好好的场面演砸了。
七十年代初,为配合破除迷信,我编排了小品《巫婆现原形》。我扮演巫婆,带领中学文艺队回我村演出。那时我的儿女刚懂事,舞台上我借了大队伙房三伯父的几个馒头当道具。两个孩子看到我往篓子里偷装馒头,回家就抢着翻篓子要饽饽。他妈含着眼泪说:“那是你爸爸演剧借的,给人家了”。惹得两孩子哇哇直哭。
|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烟台前线
( 冀ICP备13012704号-1 )业务客服:
|Archiver|手机版|小黑屋|烟台前线
( 冀ICP备13012704号-1 )业务客服: